我一直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其间有太多人声名鹊起得有些莫名其妙,他们通常有一样的留学背景、一样枯燥乏味的笔触、一样不成风格的狭隘价值观、一样平庸且畏缩的叙事表达……和一样让人觉得被激进的、崇洋媚外的大众捧得太高的文学地位。
郁达夫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他的自我陶醉超过了冰心、根植于潜意识的懦弱和散漫程度直逼徐志摩、故作大义凛然的刻板似乎想效仿鲁迅先生却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这种解读是偏激的,但当我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满满的怯懦、自卑、忧郁、自我陶醉,我实在是很难再用平静客观的视角去欣赏他所谓“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或许是现代人的苦闷,但这不应该与政治因素混为一谈甚至以政治上的进步作为主题的升华,更不应该以一个卑微自闭、敏感忧郁的不健康的少年作为第一视角。
小说并非日记,迷茫的笔触塑造不出有力的角色;人生也并非小说,没有信仰的灵魂感受不了点滴温存。
这个以第一人叙写的故事在人物塑造上的独特之处是我难以欣赏的,开场十页以内的内容,都是“我”的内心独白——或者说臆想,对于华兹华斯的诗集、圣经旧约故事等一众作品的引用非但没有起到升华和点睛的效果,更让我迟迟难以入戏。郁达夫本人在某个小土坡上抱着本诗集发牢骚的即视感太强以致于我始终无法把自己带入到故事情境中去。
这样的开端首先太不符合小说笔者建立人物时的“观众期待值最大”原则,臆想式的白描除了人物的单方面自我认知以外没有提供任何动作化、多元化的有效信息,试问这样的人物怎么立得住脚?
而在此基础之上,之后的人物发展也有了太过浓重的写实主义色彩,始终单一、封闭的人物心理空间、一直不够明朗不够具体的人物关系,让这个“我”变得更像郁达夫出于感性而写下的日记,这样的设定在故事中实在有太强的局限性。
同样是饱含个人色彩的故事,劳伦斯的《菊花香》可以做到故事的完整度、细腻度足够严谨的同时加入浓厚的个人回忆色彩,可是郁达夫的《沉沦》就真的只是一场他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故事写作水准的双重沉沦。
故事需要信仰才能让人又共鸣的余地,无论这种共鸣的来源是否正面,他都不应当是迷失的。
故事的情节块依照着“巧遇-自慰-偷窥-野战-嫖妓”这样一条一步步释放性压抑的脉络推进,但是在本质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性压抑”这个主题本身的普世价值。
每一次的情节演进中,其实都是主人公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每一种所谓的“现实压迫”也不过是一个卑微、脆弱的玻璃心自身的退却。
这让人很难把“我”的压抑和阴郁归咎于社会、国家,甚至时代……而只能将其归咎于主人公个人。在小说和故事作品中,对于一个时代的现状的讨论,应当立足于对人性、社会规律、时代背景的透析,而非对于一个人的境遇的极尽描摹。
如果现代人的性欲求与灵肉的冲突真的都像这样压抑卑微而晦涩,那么佛洛依德穷尽毕生心血的《性学三论》又该如何自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就《沉沦》一篇小说而言,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冲突构建上,都布满了郁达夫个人狭隘且过于感性的主观色彩,我无法否认他对于情绪的敏感和它所承受的压抑与阵痛,但我不欣赏他作为小说作者的创作方式,一支信仰沉沦的笔,如何给予人思考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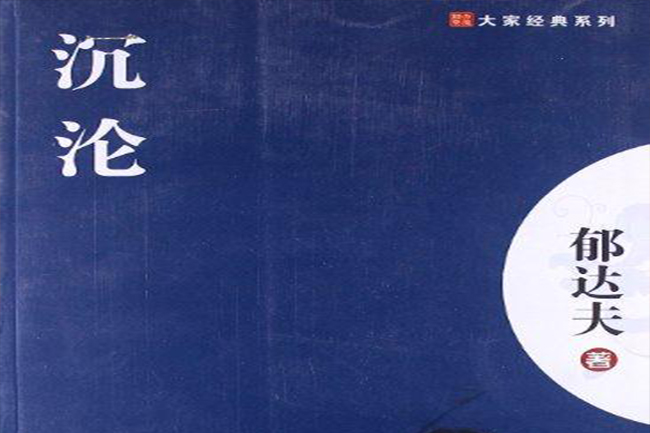
文章作者: 先锋通讯社 郑贺远
编辑者:程盟茹 黄田心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