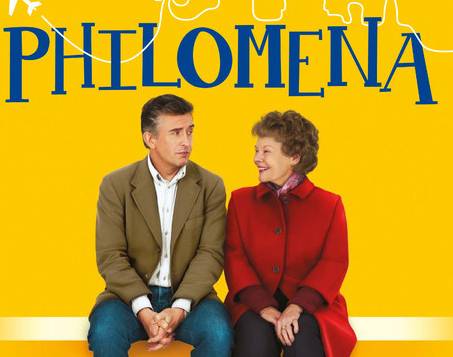
菲洛梅娜的人物原型是爱尔兰千万母亲中的沧海一粟,《菲洛梅娜》的故事也只是千万个母亲寻子的故事中不那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一切皆因注入了超越寻常意义上的母爱而让人唏嘘,同时它又用一种略带喜感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原本沉重的故事,令人动容。引用电影中的一句诗:“出发了很久以后,我们又回到原点,在那里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只不过在跟随菲洛梅娜和记者马丁绕了大半个地球之后,电影之中的他们是重新认识了出发的地方,电影之外的我们则是重新认识了一个伟大的母亲。
对于信仰的控诉
《菲洛梅娜》很容易影射到史蒂芬·金的经典《魔女嘉莉》,因为这两者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宗教信仰对于女性的腐蚀和戕害——单纯的她们在近乎无知、愚昧的情况下怀上了孩子,这之后却又因为宗教的禁锢而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像大多数人那样走入正轨。而同时,菲洛梅娜又是一个失去孩子长达五十年的母亲,于是她的寻子历程在世俗看来就成了一个悲剧的典型。
菲儿本身就是一个被家庭和亲情双双抛弃的女人,她的父亲将年轻的她狠心送到修道院之后就再也没有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有过任何联系。所以,不难理解当菲儿有了自己的孩子安东尼之后有多么珍惜、宠爱他,又是在自己的孩子被卖走之后多么无法释怀,以至于这样的思念之情在掩盖了五十年之后,拿到今天来还依然能够完全释放。不幸的是,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菲儿所在的修道院,她偷尝禁果之后怀孕,却受到了来自修女毫无人性的惩罚;她在洗衣房做牛做马熬过四年,却只得到每天一个小时和安东尼待在一起的自由时间;她在心碎之中透过窗户看到安东尼被别人牵走却无能为力,也没能为自己挣得一丝同情与怜悯;甚至,在日后她重回故地寻找孩子的下落的时候,修道院依然对她隐瞒着一切。显然,菲儿没能像《音乐之声》里的玛利亚那样遇到一群好心的修女之后活得潇洒又快乐,而是被修道院及其所信奉的宗教所压制着、毒害着,而这一点也正是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重点之一,即控诉宗教对于单纯的人们的迫害。
但是,就像电影中的那位编辑所说,“她的故事放在情感专栏周末版简直太完美了!”在这个意义和层面上的菲儿还只不过是那种时不时出现在新闻中的、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并且拿来当做谈资的小人物,很快就会被潮流吞没,被人遗忘。
两个极端的博弈
菲洛梅娜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一直都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一边是虽然曾经伤害过她但是自己现在仍然信仰着的宗教,一边又是完全从人类自身的本能出发的母性与感性。但是菲儿却一直都在这天平的两端摇摆不定,所以在电影的100分钟里我们会发现她会承认自己在修道院怀孕生孩子是“犯了重罪”,理应接受惩罚;可是另一方面她既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比如她最后一次去教堂忏悔的那场戏,一句话都没说出口,出门之前也没蘸圣水祷告),又压抑不住自己内心深处对于亲生儿子的无尽思念。所以她在得知儿子已经死去的消息之后还要在异地他乡不断拜访曾经认识安东尼的人,力图给自己的儿子描摹出一丁点在世时的肖像来。
不过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这不仅是菲儿一个人的内心博弈,更是两种相对两极分化的价值观的不断碰撞、对抗的过程。如果说修道院那一方代表了人类的信仰,以及对于宗教的无限虔诚与绝对服从,那么记者马丁代表的则是更大众化、更偏向无神论者的观念和立场——不需要宗教来获得幸福和平衡的生活,并且,除了真相什么都不相信。“上帝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欲望(包括性欲),难道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去抑制它们吗?”因此,那些天主教会才应该去教堂里发自内心地忏悔,他们不应该让年轻女子们像奴隶一样地生活,更不应该违背她们的意愿卖掉她们的孩子,何况这些丧心病狂的行为就算给单拎出来也是不能被主流社会所容忍的。马丁就像每一个观众的发言人一样,把当代社会上的伦理纲常都表达出来,并且原原本本地告知菲儿,还苦口婆心地不断向她灌输一种类似“不要原谅修道院”的意识。但是这些无常的反复并没有让菲儿从中解脱出来,反而是让她陷入到了更大的困惑中去。
宽恕是溶解愤怒的良剂
菲洛梅娜曾经这样问自己:“我的行为是罪过,所以要隐藏起来,一藏就是五十年;但是我想我把它隐藏起来也是一种罪过,因为我欺骗了别人。这两者,到底那一种罪过更深?”这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前者是在描述自己对于违反教规的悔意,后者又是在替自己为人之母的内心问责,因为这不仅欺骗了别人,更欺骗了自己。但是历史和真相不会欺骗任何人,菲尔和马丁兜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的儿子其实就葬在修道院里,只不过那些修女们故意对此绝口不提罢了。
普通人在知晓真相之后一般都会选择像马丁一样,跑到修道院那里大吵一架,指着那些贱人痛斥一番,然后要求邪恶的修女们公开所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并作出道歉和补偿。这基本上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的大快人心的情节,也是社会伦理道德教给我们“邪不胜正”的不变真理,但是菲儿在这最后关头却没有选择成为这样一个愤怒的发泄者,而是淡淡地对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说了句:“我原谅你了。我只是来看我儿子的。”相信在那一瞬间,菲儿已经在寻找自己儿子的过程中找到了最终的平衡点,她既没有继续扮演一个惹人同情的受害者的身份而对于这件事避而不谈或者不敢面对,也没有像马丁那样暴跳如雷恨不得将对方先杀之而后快。她把自己皈依、信奉的宗教和人之常情的母性统统吸收进自己的小身躯里,因为她明白就算把修道院夷为平地也换不回自己的儿子,经历了这么多的身心折磨,她现在只想尽情消解自己那份埋藏太久的骨肉亲情。当马丁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口气问菲儿“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是很生气!”的时候,老太太也只是云淡风轻地回答道:“你不知道我走到这一步有多难,但是像你那样生气,一定很累吧。”菲洛梅娜用自己的宽恕折射出自己内心的坚持与单纯,也同样靠这一份对愤怒的溶解找到了自己日夜牵挂的孩子。现在的她,只在乎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那也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尊严。
影片结尾处,原本不信教的马丁突然买来了一个耶稣的小塑像摆在了安东尼的墓碑前,这时导演想要借此表达的情感内核迎来了第二次爆发——其实我们都是愤世嫉俗的马丁,但未尝不可像菲儿那样,放下无谓的愤怒,让包容渗透进自己的骨髓和血液中。
文章作者:先锋通讯社桐乡分社记者 郑永杰 编辑者:李莹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