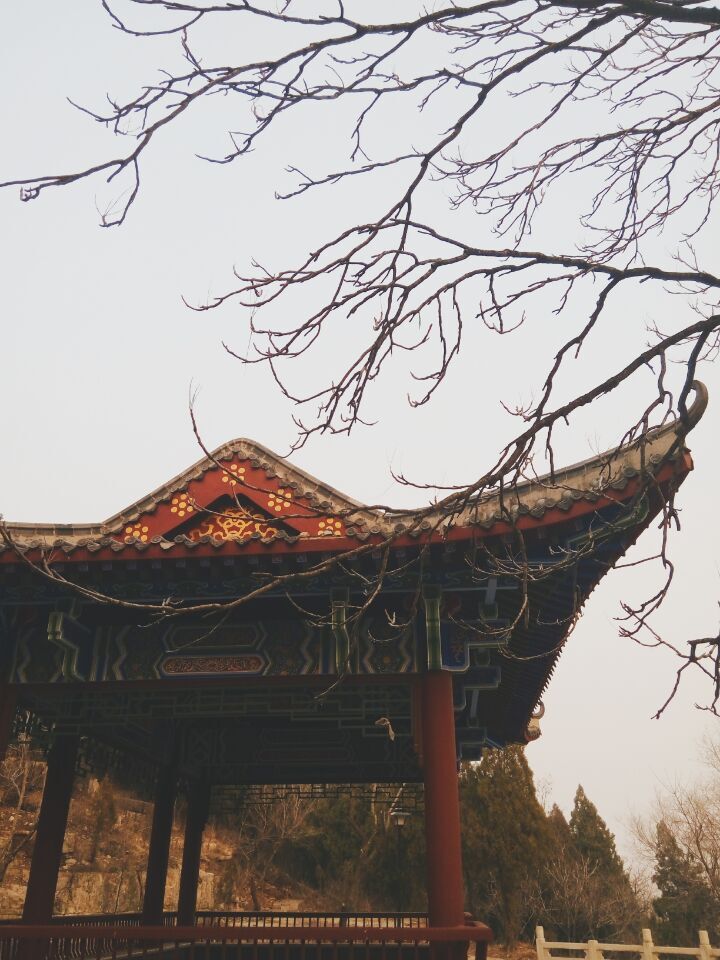回忆是深海,透过残忍的冰冷怀念自己。人总会遇到能够拥抱取暖的人,只是你要等。之所以会感觉失望沮丧也只是因为剧情没有向我们想象中发展而已,零下十二摄氏度的水早已冻结成冰,抱怨没有办法用来解渴的唯一办法是用体温融化它。
只要你愿意。
不去思念作为回报是区别于遗忘的方式,有力、坚强又让人觉得潮湿黏腻,带着一点病态的精神满足,各自生活。在接到从她那边拨来的电话之后,心却因为疼痛变得麻木,在轻声的回应出那个“嗯”之后,全身燃起对自己的愧疚,就像是在胸膛里填进一块火炭,一点点炙烤血肉,由内而外的煎熬。去慢慢回应那句“你好吗”。
月光透过半掩的厚实粗布窗帘点亮了房间,能看到地面上雨水反射过来映在房顶上亮闪闪如同溪流般的光影,数字默念到267便放下思绪,用细弱的胳膊支起身体愣愣地做起来,转头看看一旁的窗,光线亮的柔和但还是微微眯起了双眼,墙上的钟清脆的响了3下,我有些无奈的用手轻轻柔柔眼睛,披上搭在椅背上的格子衬衣径直走到窗前看雨。
天还是暗暗的墨蓝色,清透里掺了一点点紫,雨水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拉起另一半窗帘,瞬间断了电的开关般整个房间黑下来,眼睛在这样的黑暗里慢慢的调整适应,视界里满是密密麻麻灰白色的星点,太阳穴传来突突的跳动感,最终一切恢复正常。
你好吗。
感激缘分这系统,我们的回忆里没拍下太多的泪流。我们刚刚相识的时候在一起放学回家的小路上,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空气里总是飘着花朵奇妙的香气,莞尔之间遇到的朋友是一种很奇妙的心事,于是要把所有的欣喜和庆幸满满装进口袋,随身带着生怕遗忘,那年我们是前后桌,她转过头来对我笑的眼睛弯弯的好看的像晚上闪亮的月亮。
我是C。
嗯,我是Q,很高兴认识你。
对于我这种生性冷淡不懂交流的人,面对别人的招呼总是不由自主从内心深处升腾出一种叫做“说话好麻烦”的情愫,但是当面对眼前这个漂亮干净单纯可爱的小女生的时候,觉得原来对话可以是这样惬意的一种享受。
我交朋友了。
因为家住在同一个方向,上学放学约好一起作伴,那时候大概是两个人之间感情真正开始相互融合的日子,那年我们高一,十五六岁的年纪开朗灿烂傻里傻气得刚刚好。我留了一头极短的蘑菇头短发,而她是个长发及臀的小个子姑娘,兴许是从那会遇见她开始从她身上看到了长发的美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续出了一头飘逸的长发。
生活无时无刻都因为彼此的出现而发生些星星点点微妙的改变。
在我们最放肆最有梦想的时光里以梦为马,孤筏重洋。
当她在某天发现我的桌洞里有其他女生写来的信件和买来的礼物的时候,像只被戳破的气球一样地对我爆发了,我站在那里愣愣地审视着存在于她身上可怕而又可怜的占有欲,一瞬间觉得可怕而寒冷,在那些日子里选择对此逃避似乎是最便捷但又最麻烦的方式。
她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收敛自己身上的戾气,但也为了弥补我们友情之间出现的嫌隙写了无数的信件给我,提前等在上学的路上,洋溢着带点歉意的笑容,我们重归于好,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她所给予的感情分量太重,重到好似有大石块压在胸口有窒息的感受。在无数次面对她歇斯底里过后,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和欣赏。那个自己已不再是昔日里害怕跟别人打招呼的我。
这改变因她而起,这结果也因她而生。
我在那个路灯亮的晃眼睛的日子里对她说,C啊,我们好像不能在这样下去了呢,我们不能再继续做朋友了。说完这话的时候胸膛里的气息断断续续喘不上来,眼睛里的泪水咕噜噜打转,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也只有付出这样让人心酸的代价才能让心平衡。她说,我从来都不缺你这个朋友啊。然后转身就走。
她哭了吗,我看到她的在路灯照耀下小小的身影一抖一抖,细碎的灯光像是洒落了一地的星辰。就在我们一起来来回回穿梭了无数次的这条路上,好像那些日子里的欢声笑语打打闹闹一股脑全都冲进脑海,炸裂一般地疼。
一起买来的日记本里所有记录里都有她,所有的摆件都有我们一起挑选的回忆,就连上课用的笔记上都有她的字体,方方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还有那句“Q你永远都是我的”。直到我在校园里看到她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才彻底对她的心情感同身受,相遇的时候也只能擦肩而过低下头。其实我真的很想说一声“你还好吗”。
我很想念你。但是对不起。
时间总能抚平旧日的伤口,我们互相争吵歇斯底里的记忆被渐渐磨平,筛选留下的只有那些让人回味无穷弥漫着青春狂热放荡不羁的美好时光,那样的你是那般美好,长长的头发总有好闻的洗发水的味道。在我们各奔东西的这段日子里总能收到你的来信,我并不清楚你从何处知晓我的所在地,但我知道我们都存在在彼此的心里。
你在信里说,那些日子真是抱歉,但心里一直以来都是温暖。
我也是啊,我如此这般回复着你,问你现在好吗。
于是你从遥远的北方拨通我手中的电话,轻轻地说了一句“Q啊,我很好,你好吗?”
“嗯。”